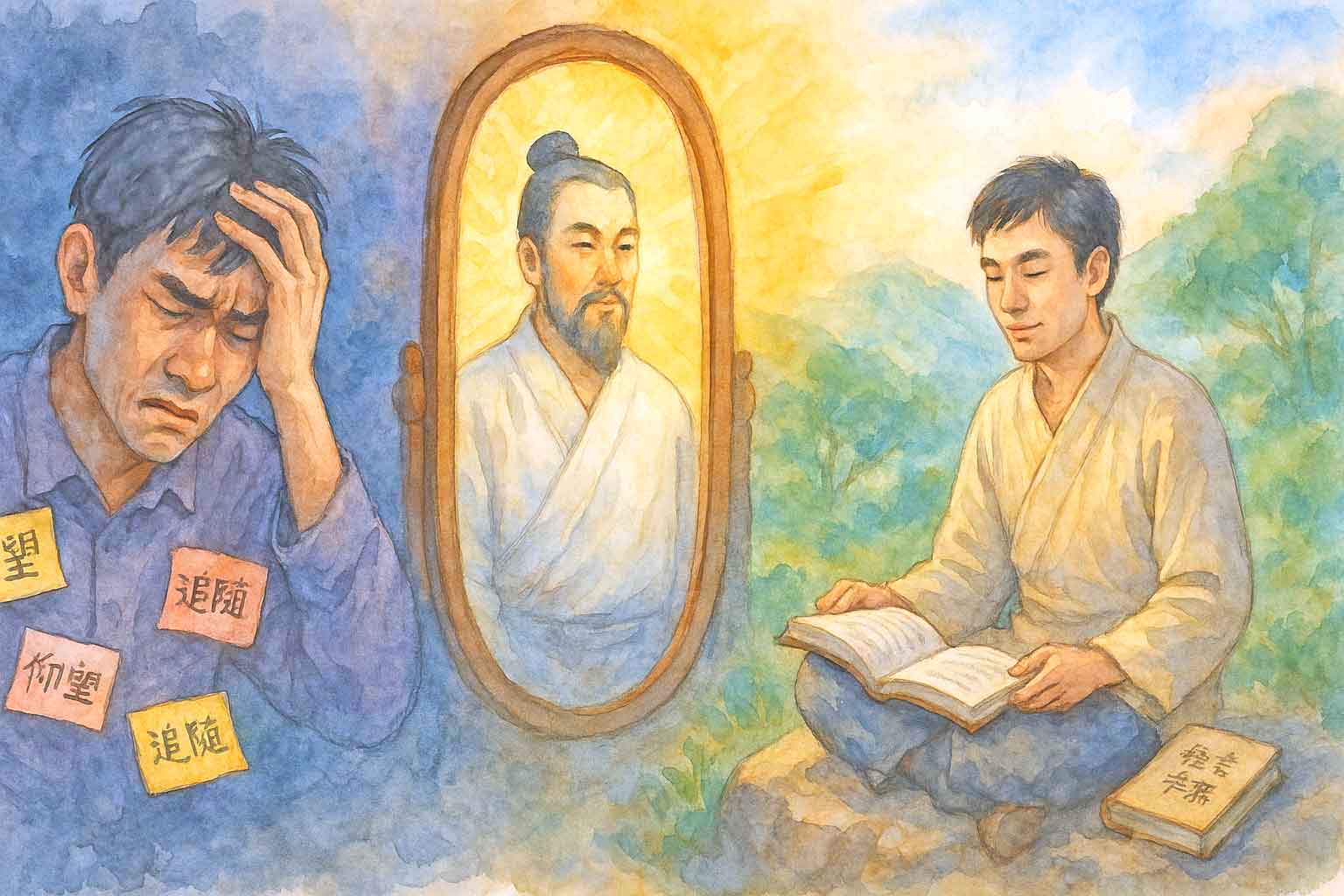
马征:因为你都不了解他的一切,只做表面功夫的文章,假如是你的朋友他会和你好吗?你首先要知道,自己也可以成为圣人,不用来生来世,就在当下。因为你的思想距离圣人越近,那么你就越像个圣人,起码样子是有了。相反成天的溜须拍马,假装崇敬假装努力,心里一次都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,读书读到地老天荒也是自寻烦恼,怪不得别人
学生:这句话是太感动的启发。尊重确实是遥望的距离,反而喜欢的人事会各种想靠近了解。
马征:你可层想过,天天生气,你也可以接近圣人?这话一点都不是疯话,而是大多人都用错了方向,我所说的生气,甚至生大气,是对自己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堕落?为什么这么笨?为什么这么懒?为什么这么随意?为什么胡思乱想?就像五行生克中的“相克”一样,很多人一听到相生就开心,因为这样往往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吗?但听到相克就皱眉,甚至不开心。但真相是,“相克”是为了制约相生太过后而失去“丨”的平衡所生的,当你真心为他好的时候,这种破坏力就是正能量。
学生:衷心感谢师父的“斧”正。今晚静坐,我要好好“生生气”。
马征:我这些阶段也都经历过,不过很快就过去了。原因其实很简单,当你查一个字的时候,我一开始就是几十甚至上百个字,并且在我们都不懂的时候,我用100字要求自己,因为我相信自己和圣人有同样的才能,我不是想一辈子求学的,所以我一边查一边给你讲了接近两年,同样学习但要求不同,结果也注定不同。
当时你觉得我讲一个字很开心的时候,我就在用100倍要求的自己,现在你觉得原文数据重要的时候,我仍然再用100倍的大数据要求自己。所以我才会一直和你说起点一开始就要和圣人一样。有些人对于这样的要求能够欣然接受,有些人会觉得就像受到了精神虐待,这都很正常。这种搜集大数据,并且给身边人演讲的能力其实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常态。
在美国,日本,英国,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全部都要写论文一样的调研报告,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生,等这些孩子在小时候习惯了,到了初中大学他们就能收集和整理世界范围内的论文和著作了,其实他们在小学时候就已经是个小专家了,这就是一种收集信息的能力,人人都需要。
因为每个人一生的时间精力有限,所以当下做出的判断也有局限,搜集数据就是为了打破当下局限的,所以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从天培养这种能力,我也只是学习了个皮毛而已,其实真没什么好讲的。我经常感慨自己真的就像个人家的小学生一样在搜集数据,也不存在谁的智商高,谁的情商低这种问题,因为习惯就好。
学生:教育之基础的束缚,这些话我完全认同,也是深深厌恶自己的地方,也是不想再在中国养一个孩子的根源,这个有点扯远了。身在其中,又曾是小小既得利益者,所以在一大段时间都在挣扎着出圈,但与师父不同处是离开这个熟悉的模式会下意识里害怕。北方人之山东人格外如此。十多岁到三十岁都在叛逆期度过,但遗憾的是最后妥协了。在朋友的生死告别课上,最后一次叛逆只是选择了换个行业度余生。
回头想想,为了探索生命本质的初心还在,但更多心力被消耗在医学学习和内耗里,好像还不如学医之前有生机。记得当时发誓要用十年暂别红尘的热闹,先好好学习,于是关闭了对外界的大门,麻木的游走在各个学习班,师父是我这些年唯一一个精神世界里连续存在的良师益友,也是我与“叛逆心”唯一一条链接的线索。如果没有遇见你,我都不知道十年学医后会变成怎样的灵魂。其实中医这个圈子的人比较无趣,或者说有点群体性自私,可能这个行业冷了太久,“穷”了太久吧。
相比较我之前的金融圈,没有团队意识,不追求创新,突破与成长,更没有看到那种真正的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——而最后这点是最初最吸引我的中医文化。我对中医的爱,跟东明师兄对中医的爱差别很大,或许对于一辈子以此为行当的人而言,中医承载了赚钱养家,社会尊重和人生价值体现等多重意义。而我的唯一压力,是既然选择了,就要认真负责,对自己对患者都要认真负责。看病只是工作习惯决定,远没有学习生命的心安理得满足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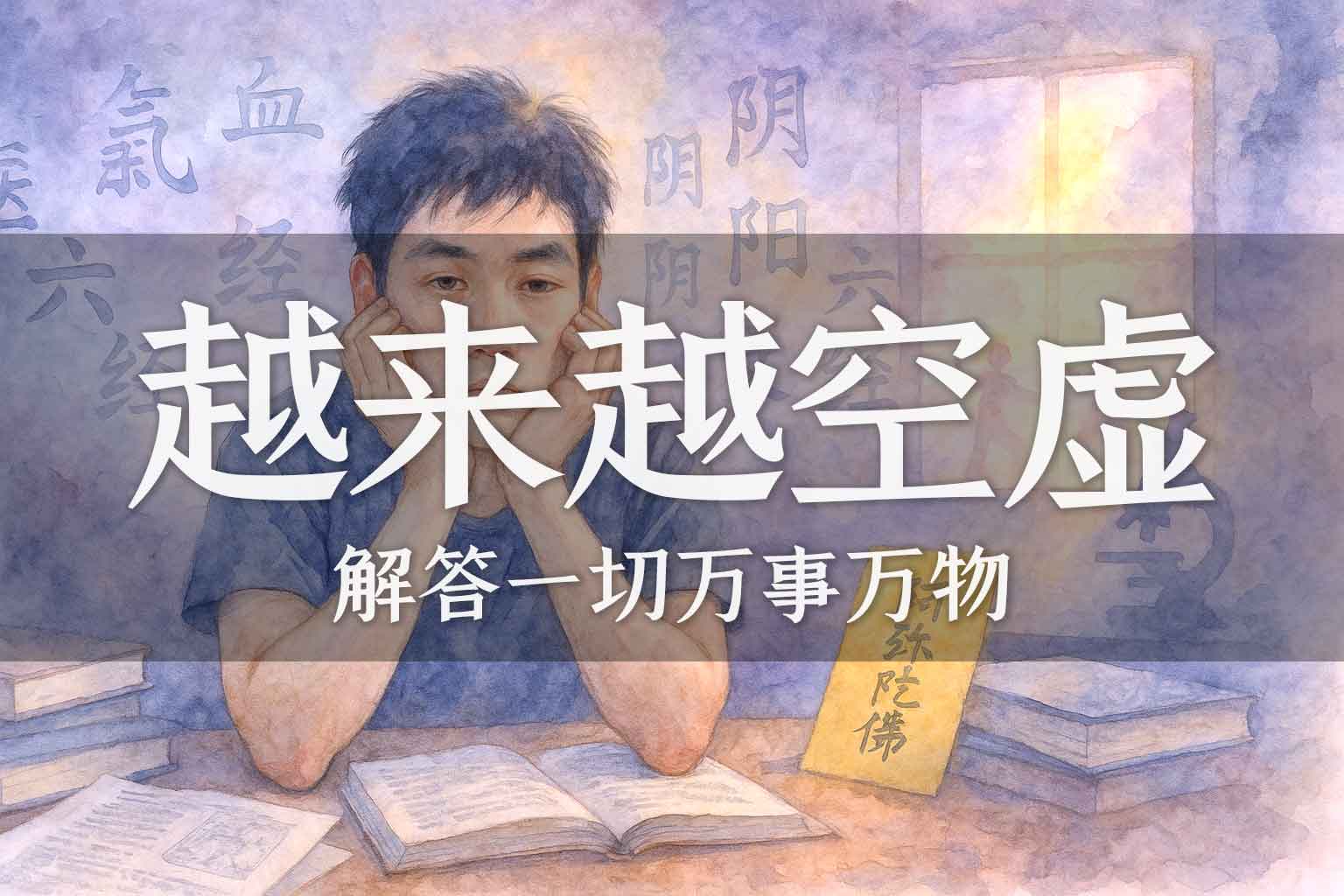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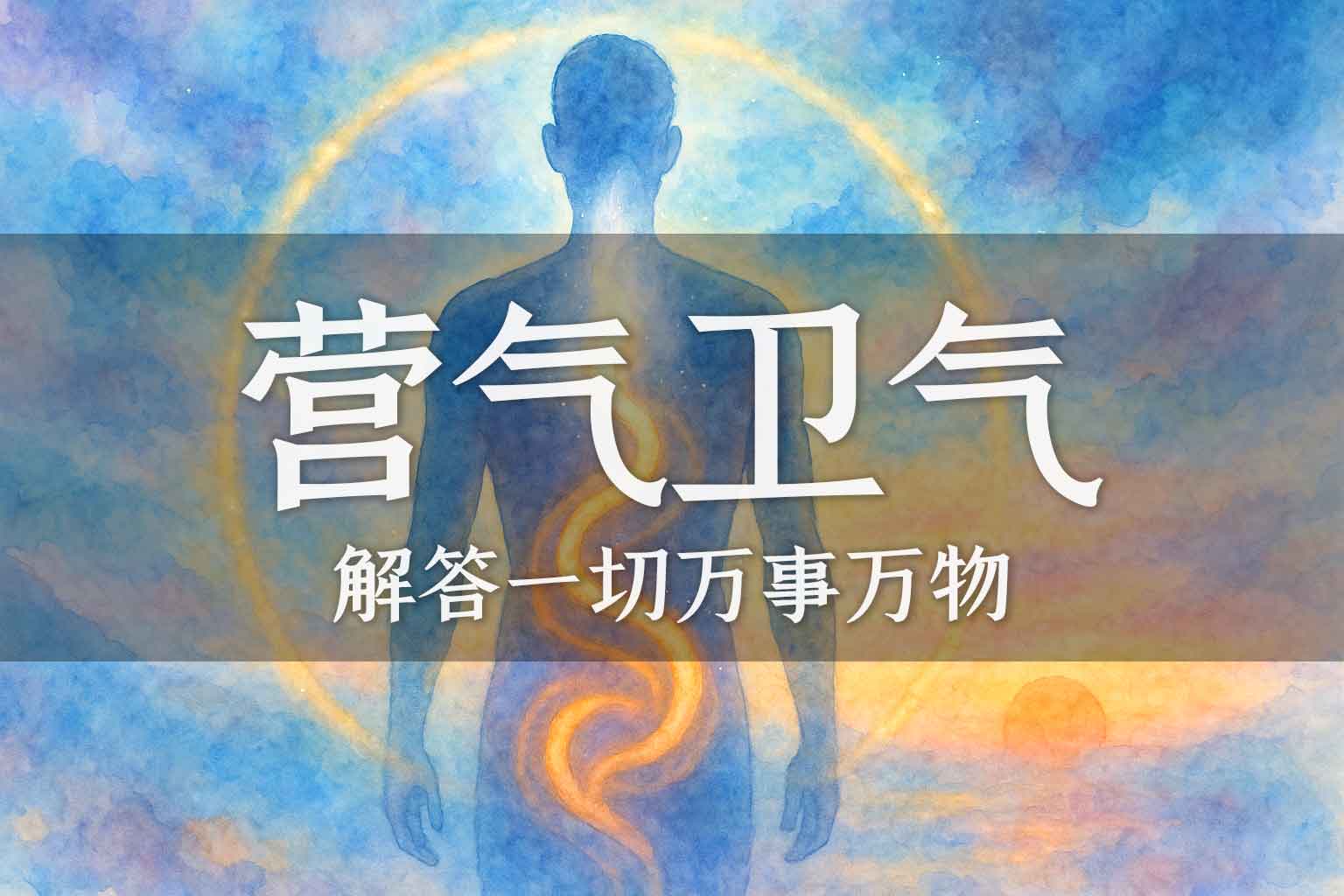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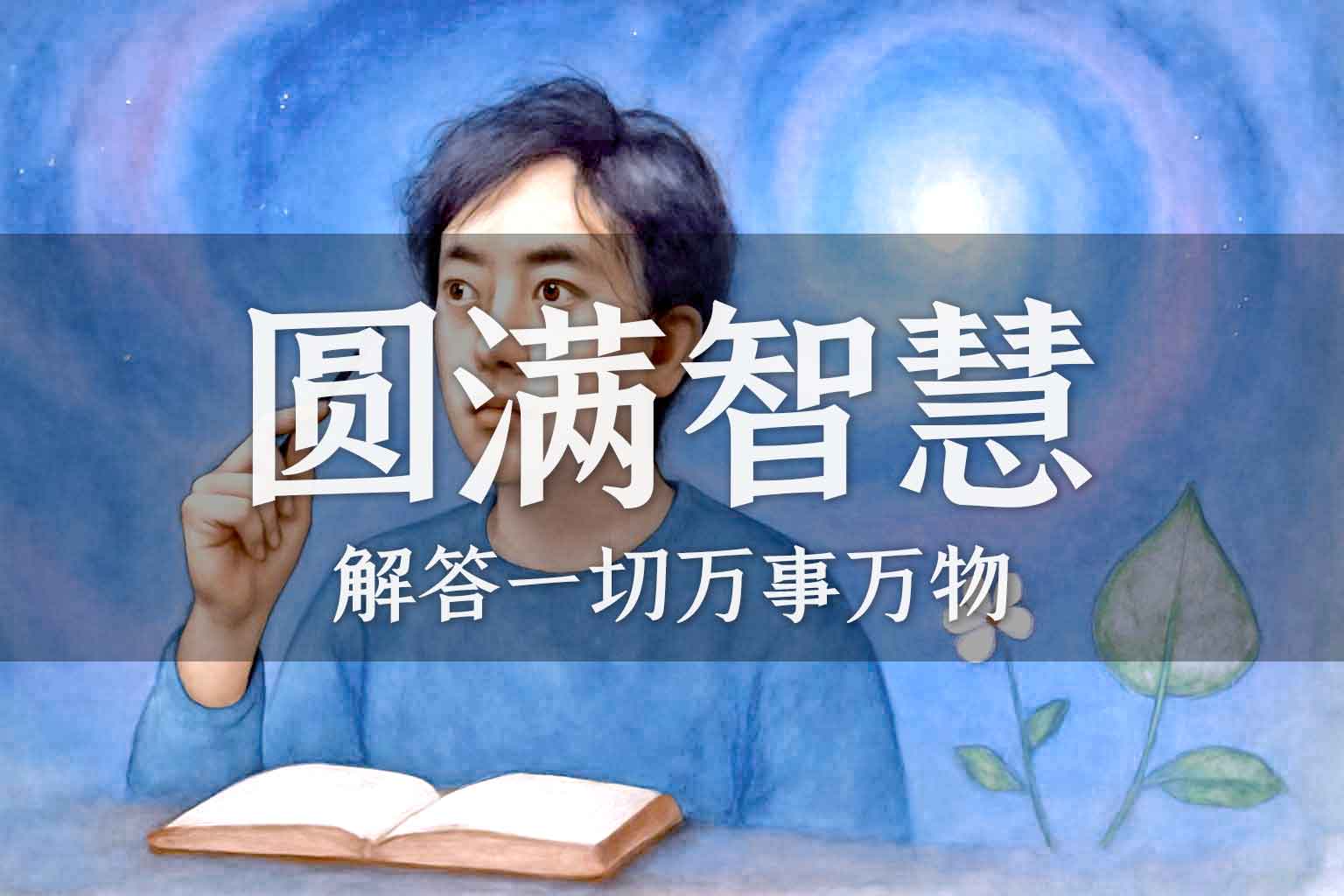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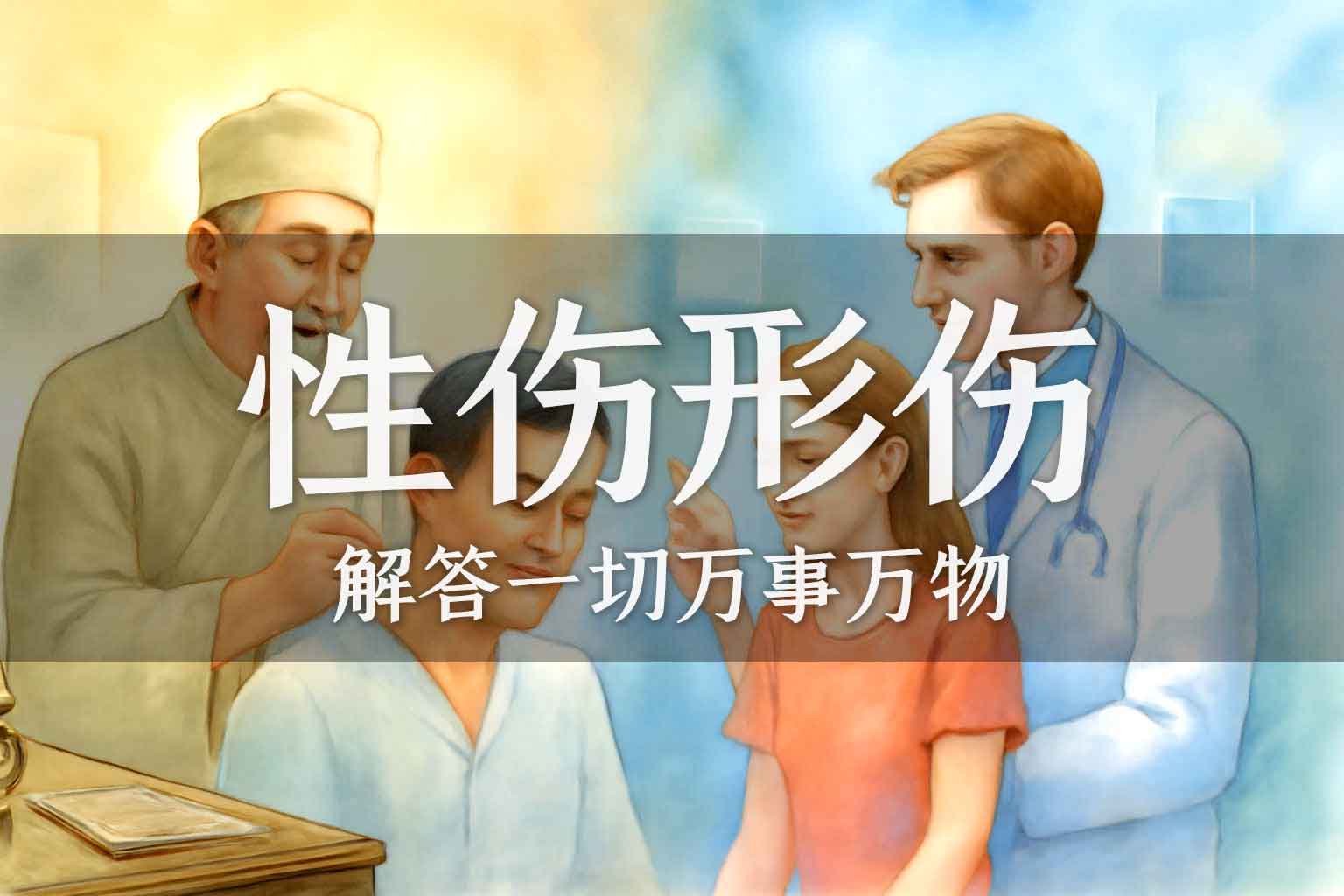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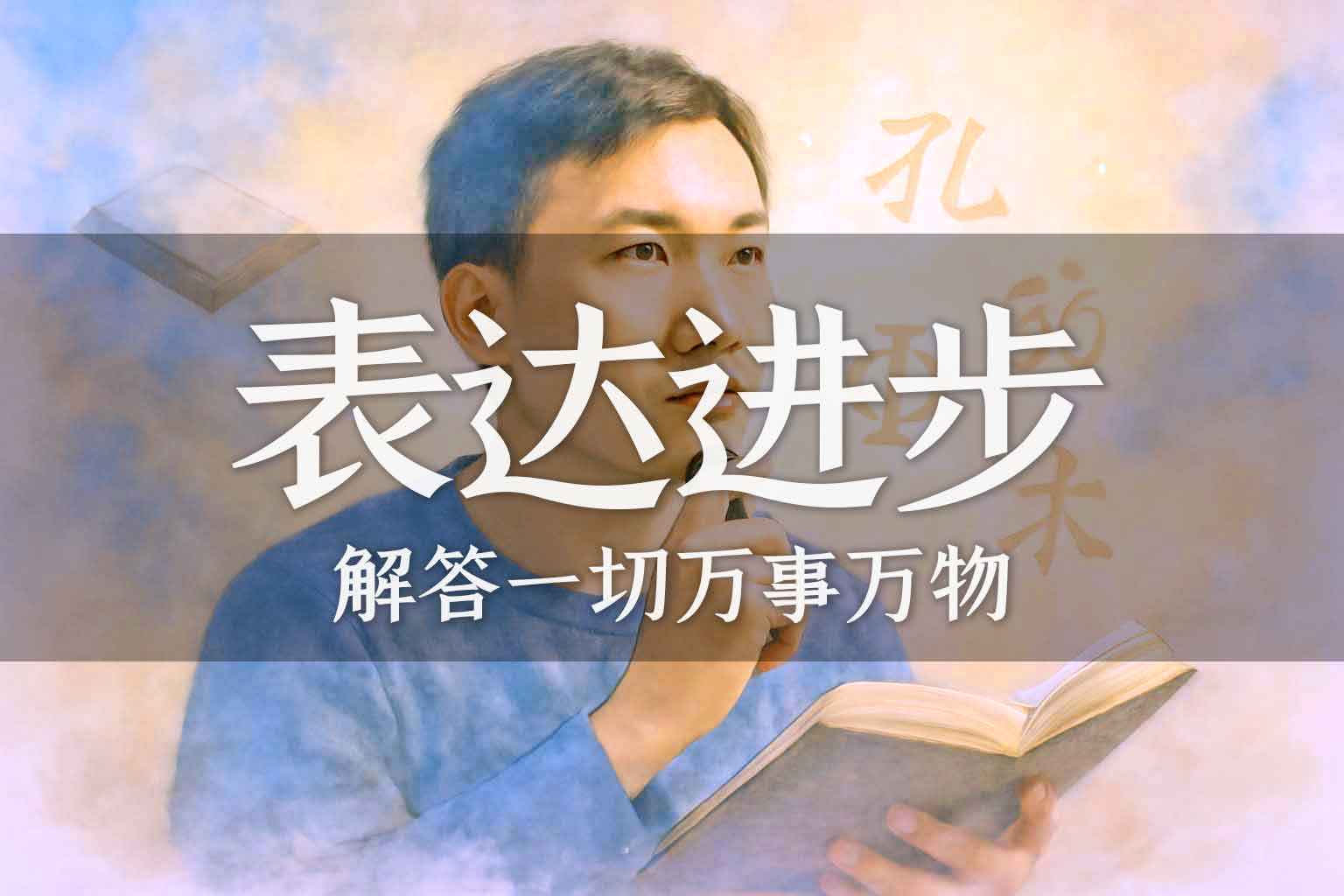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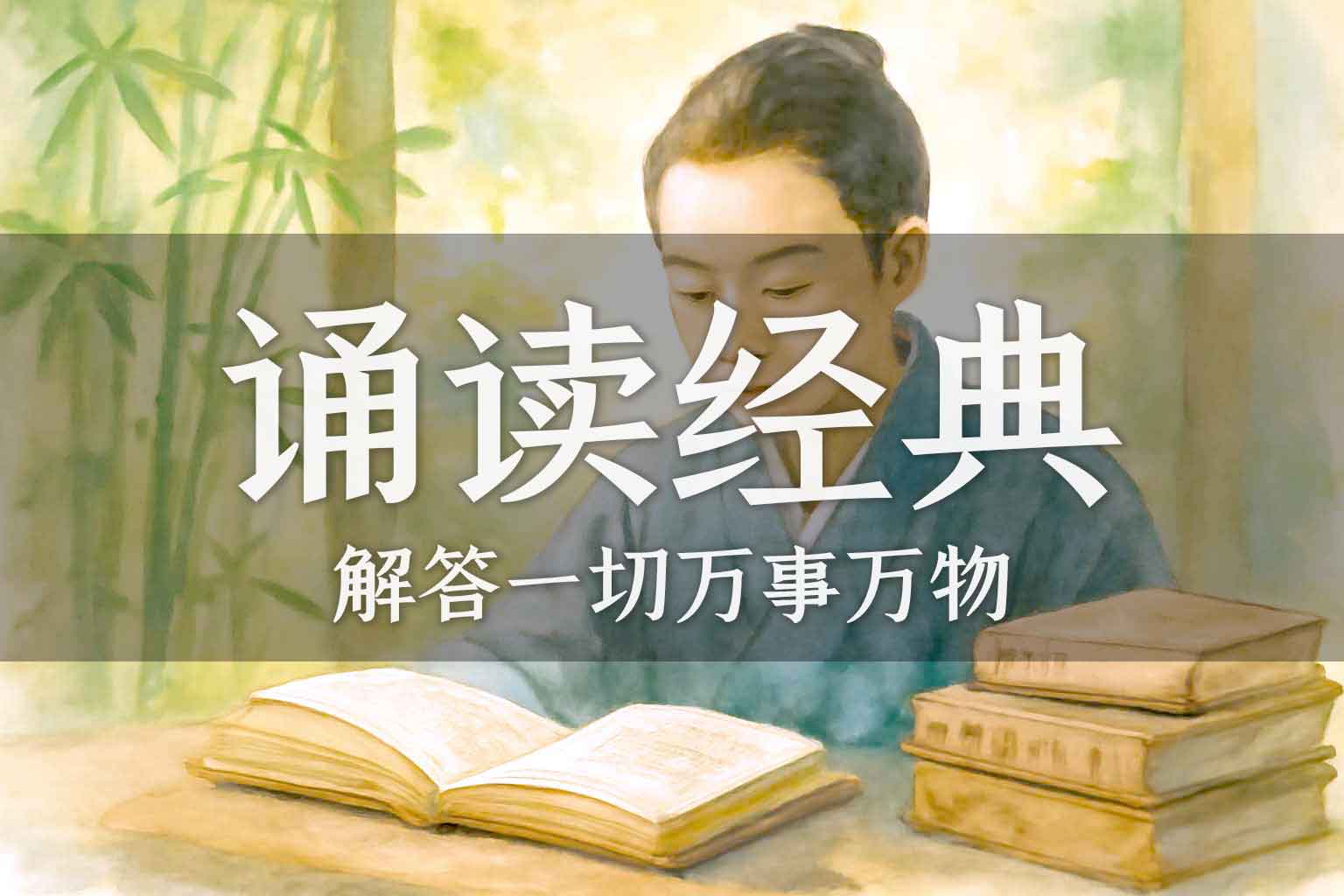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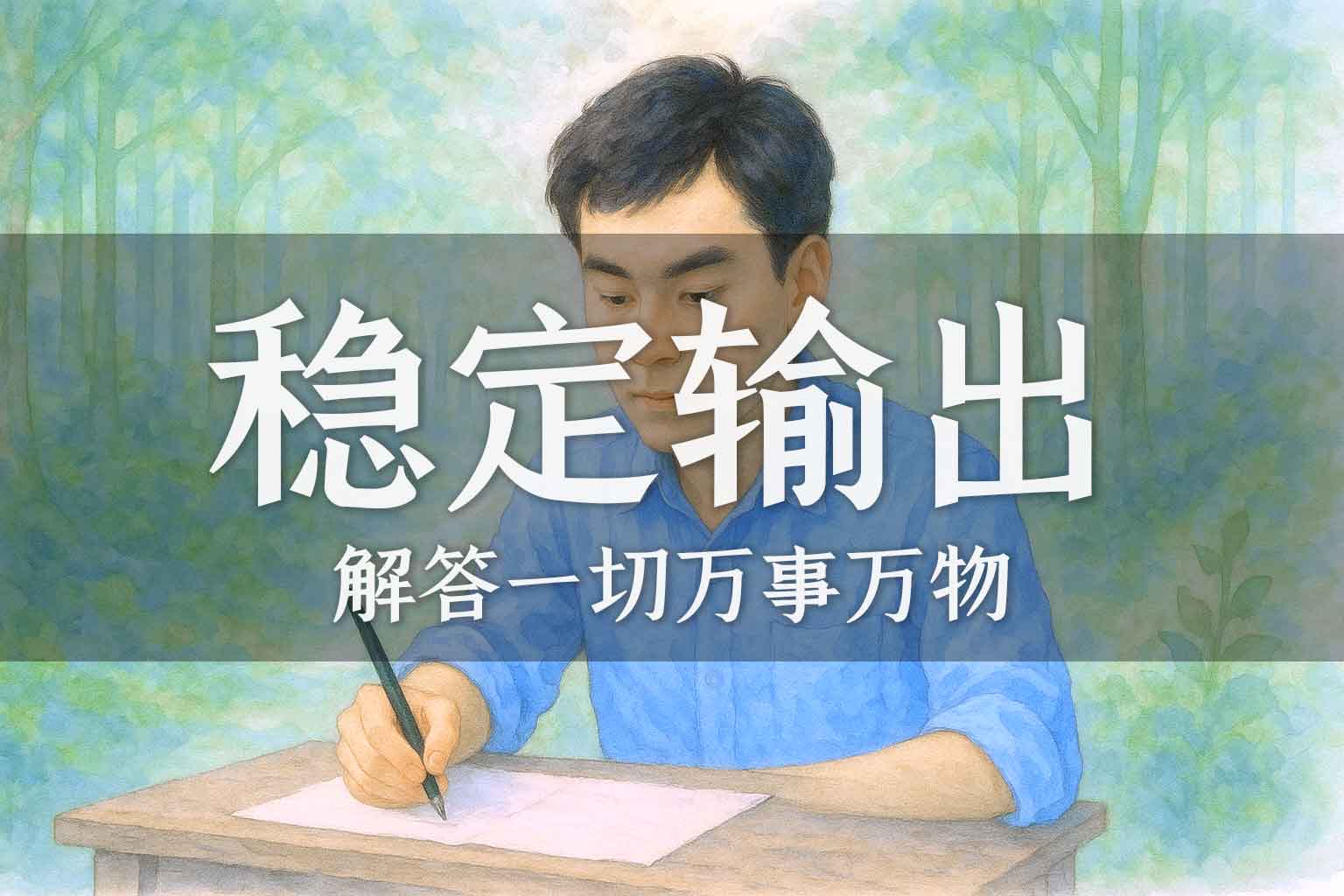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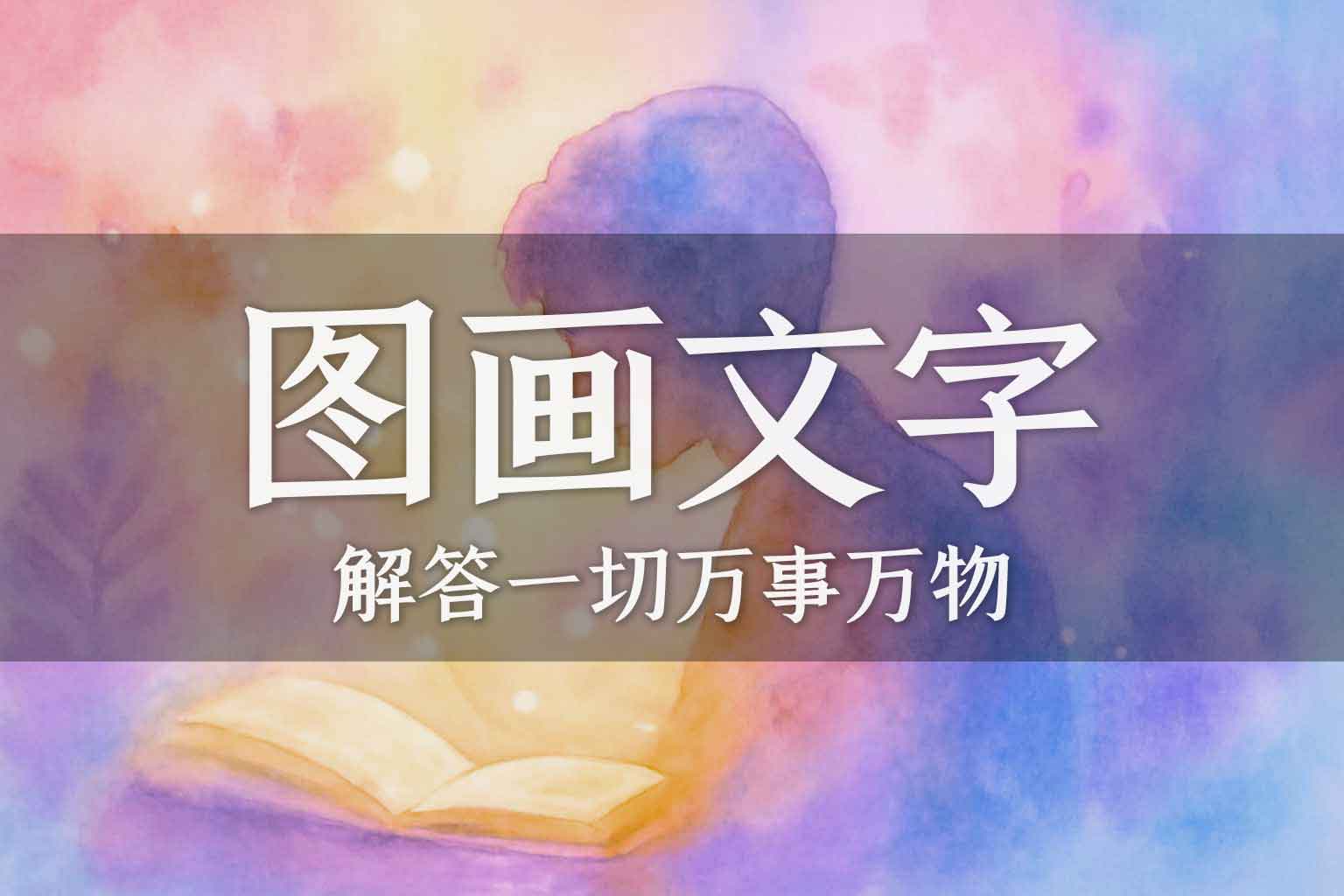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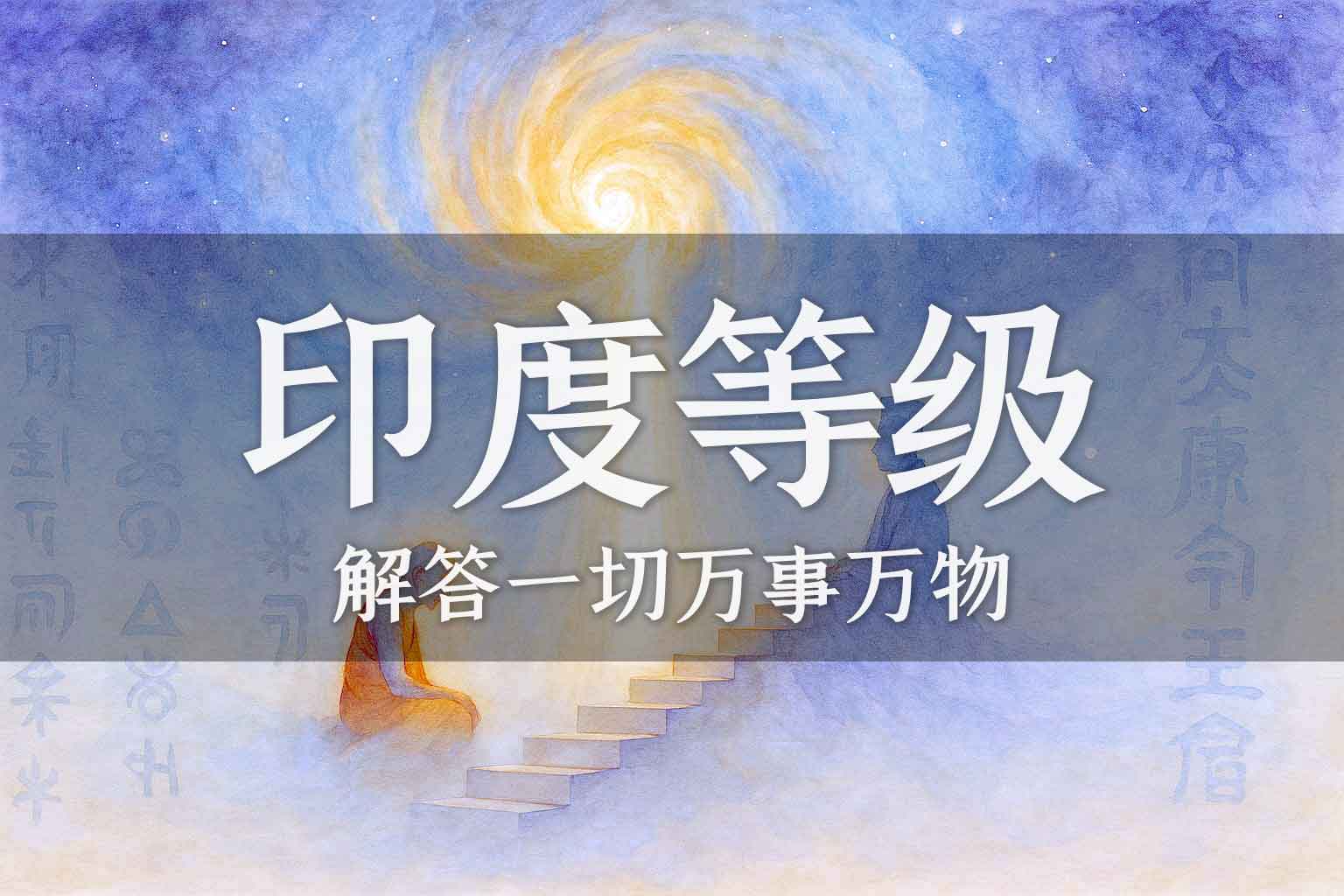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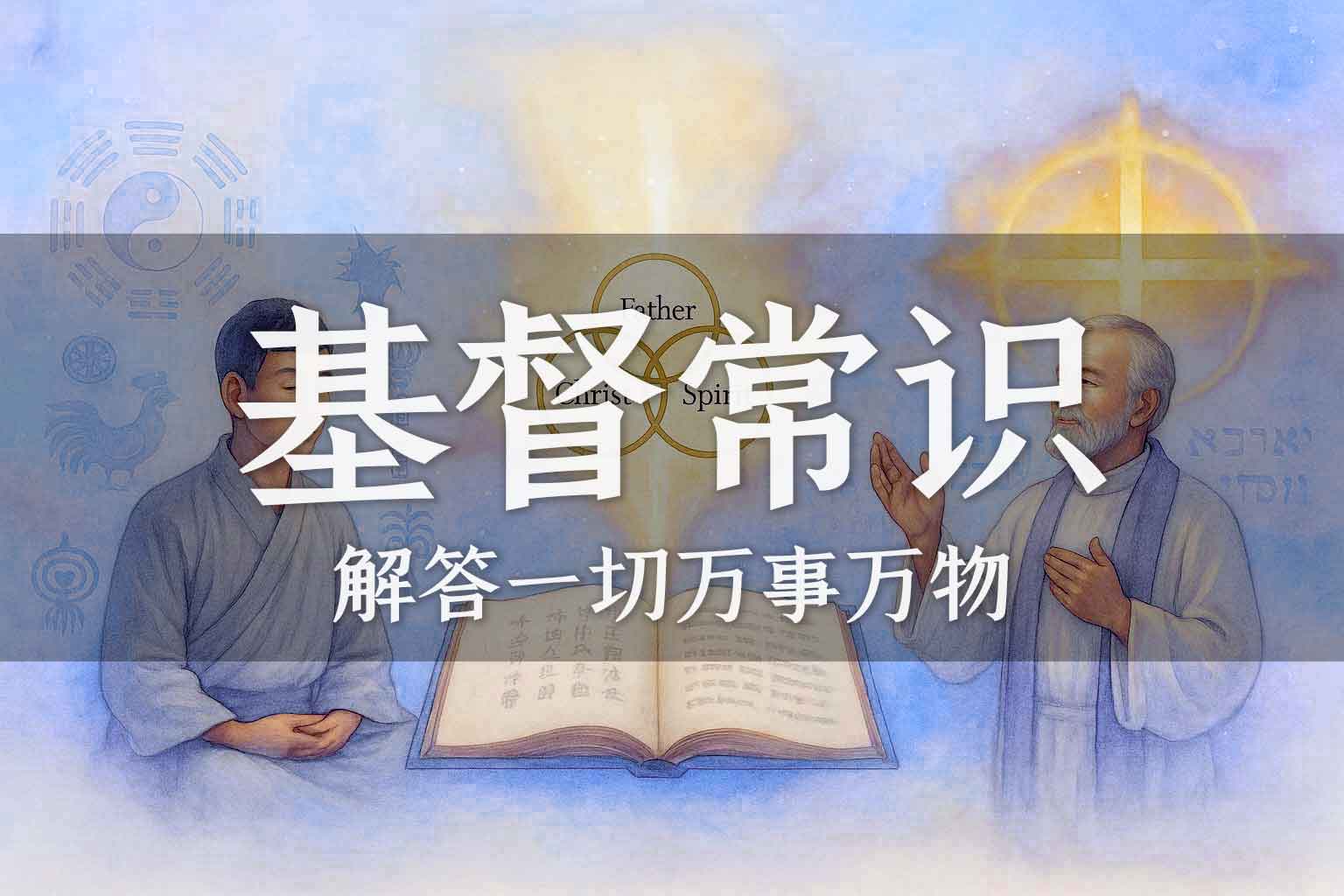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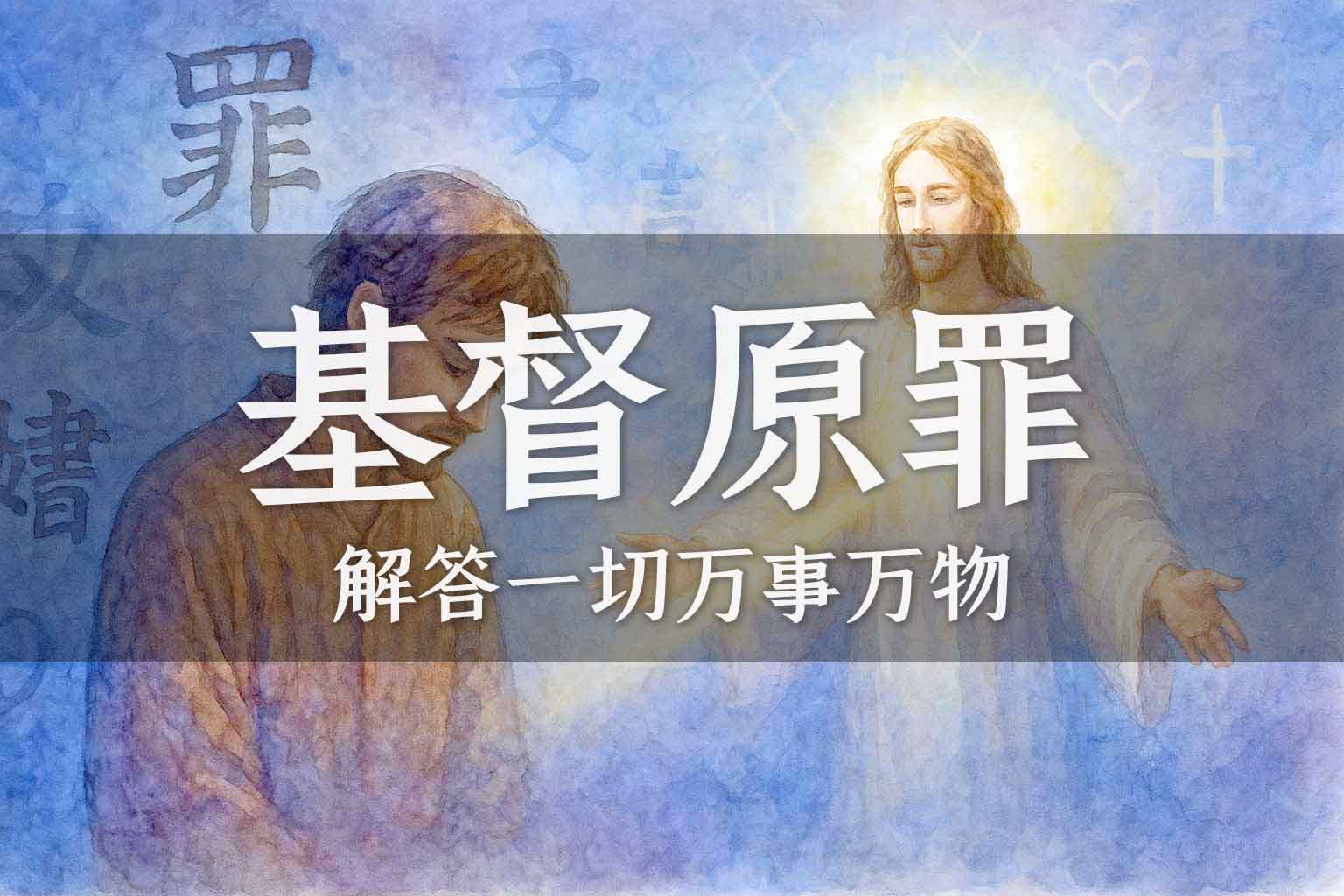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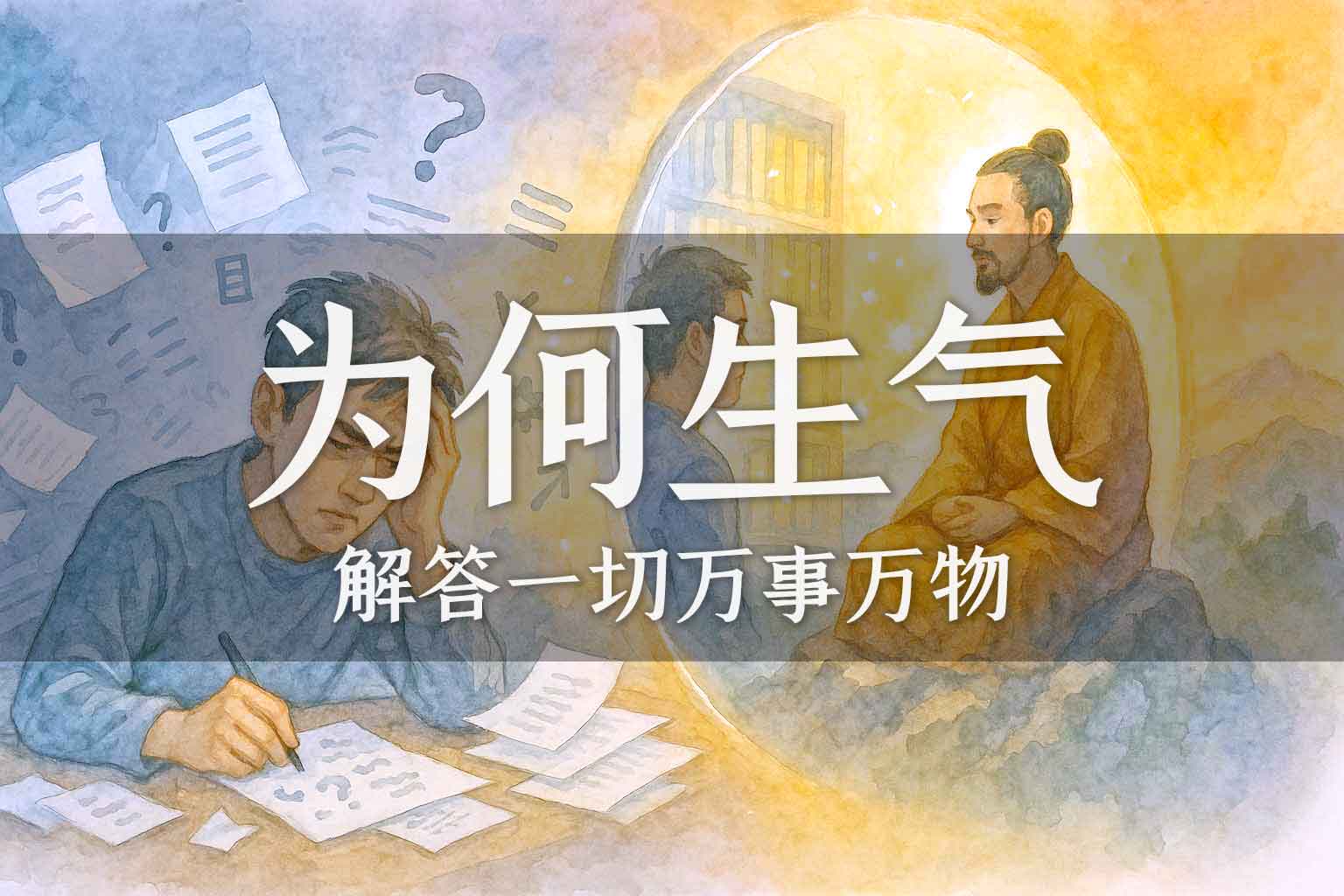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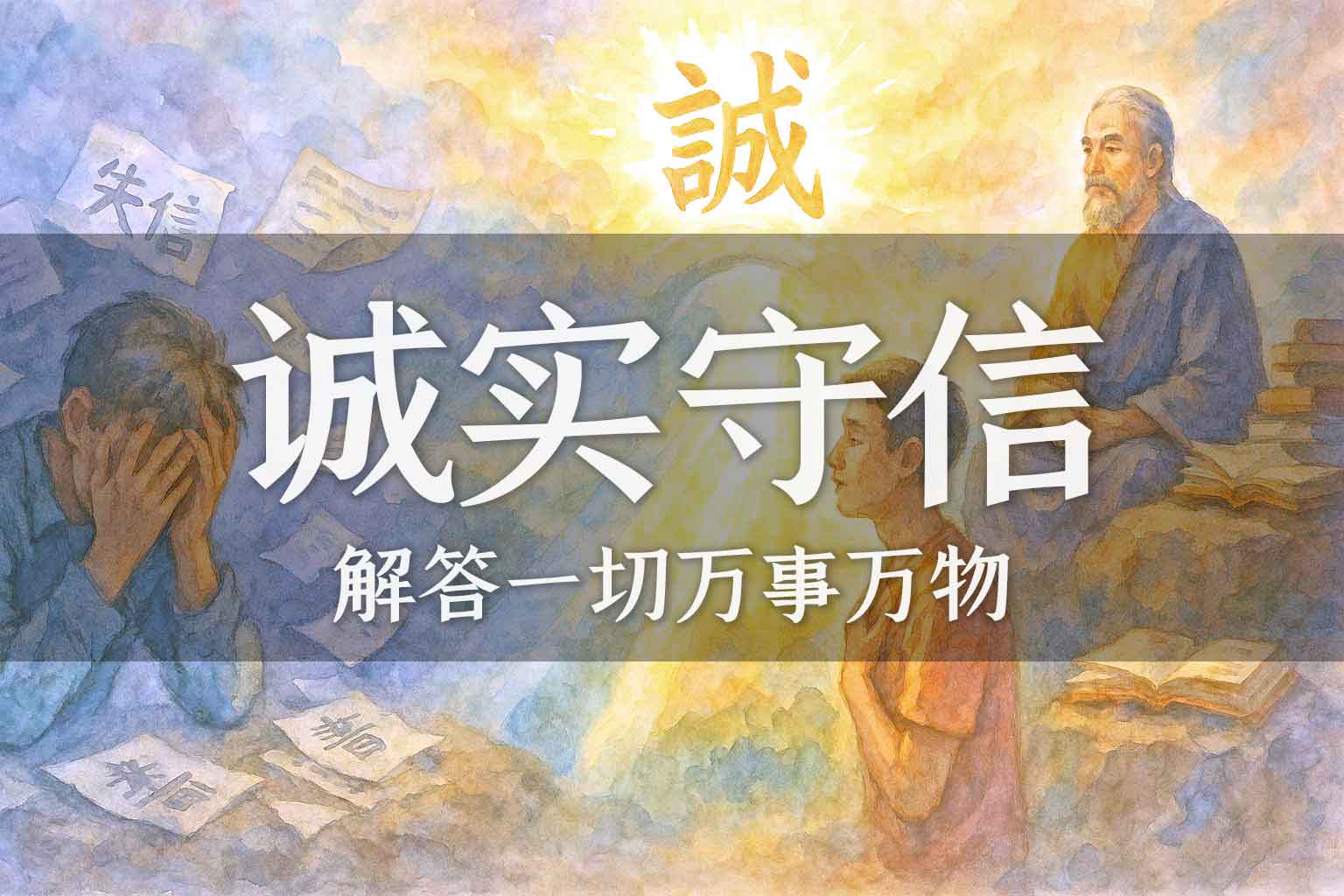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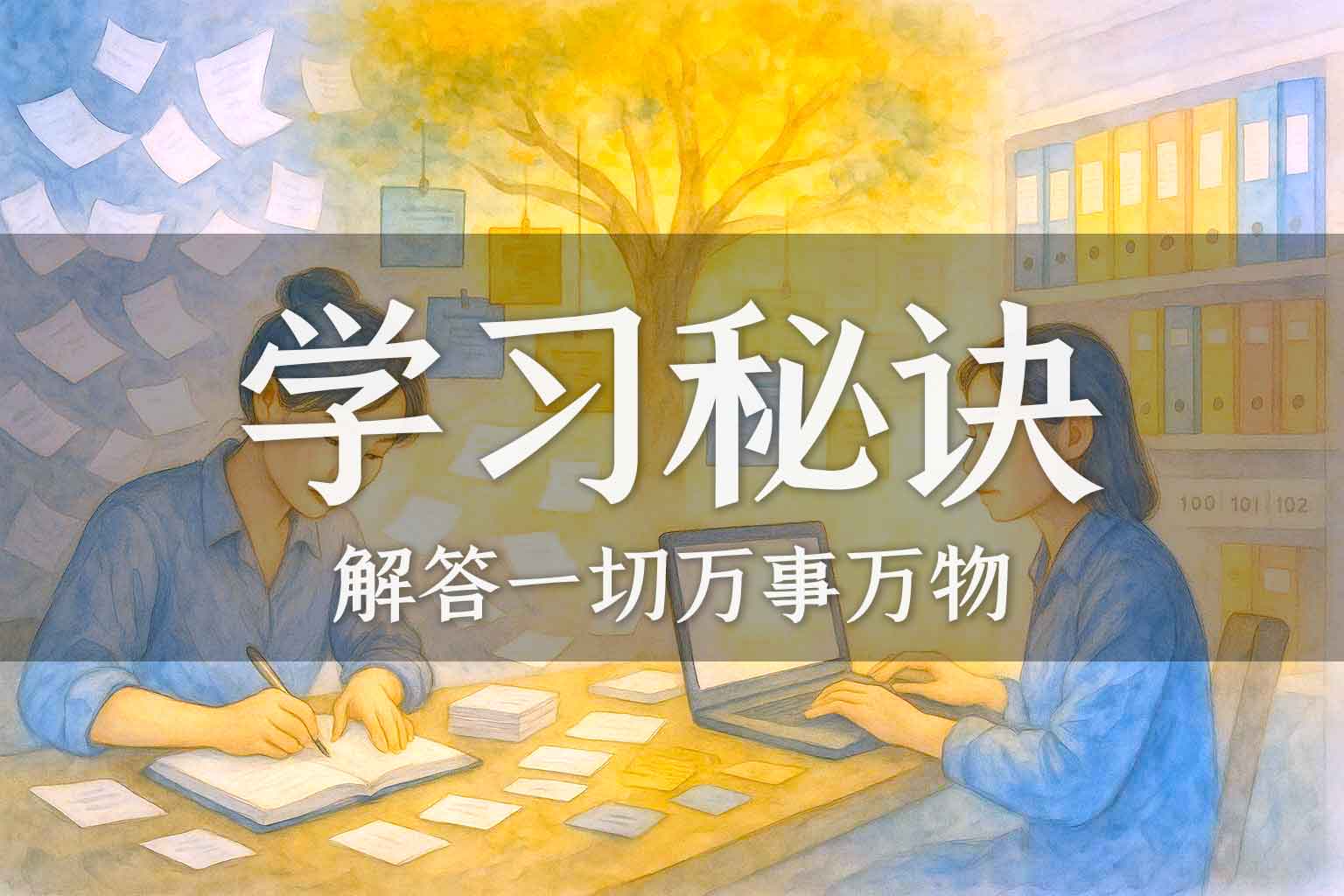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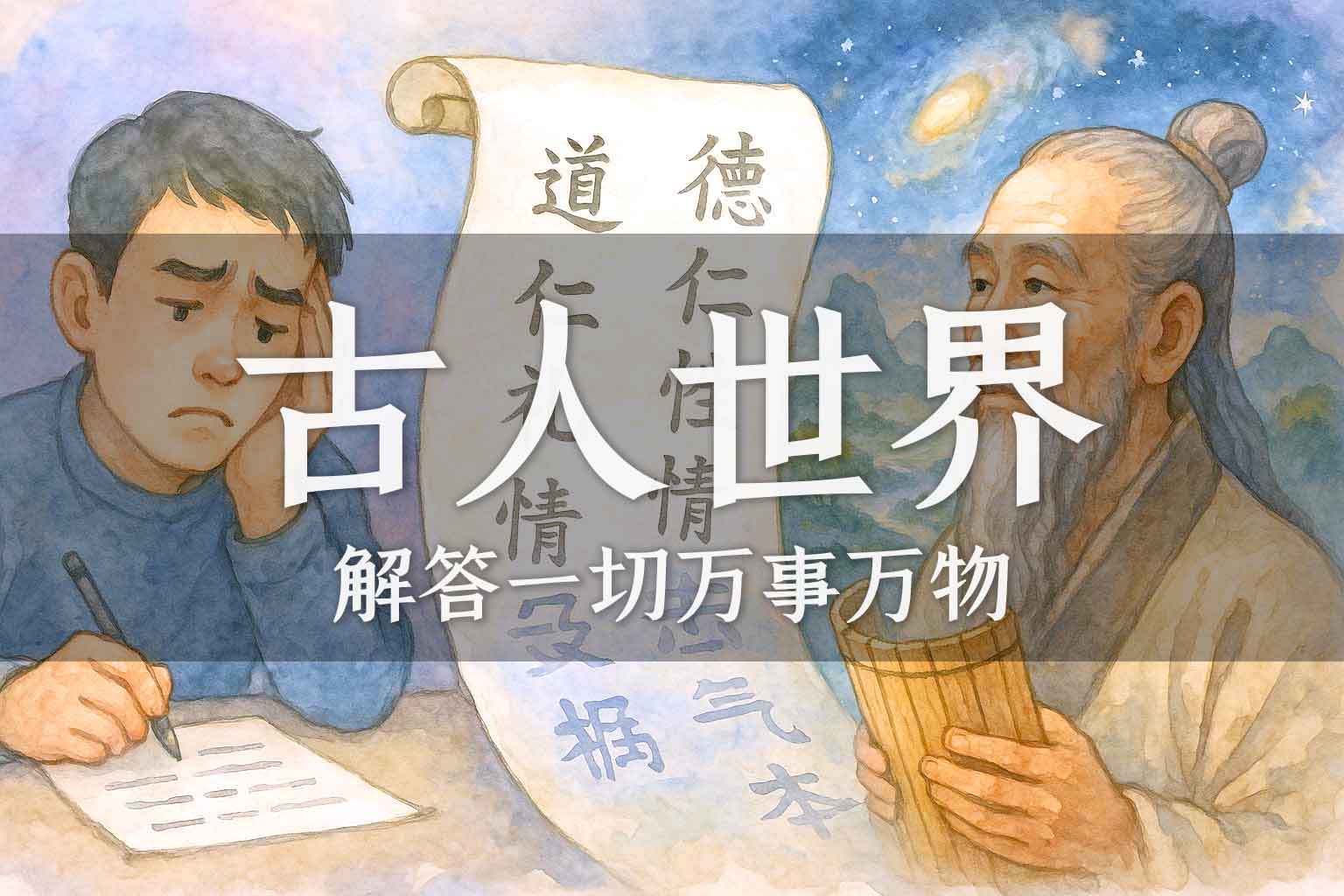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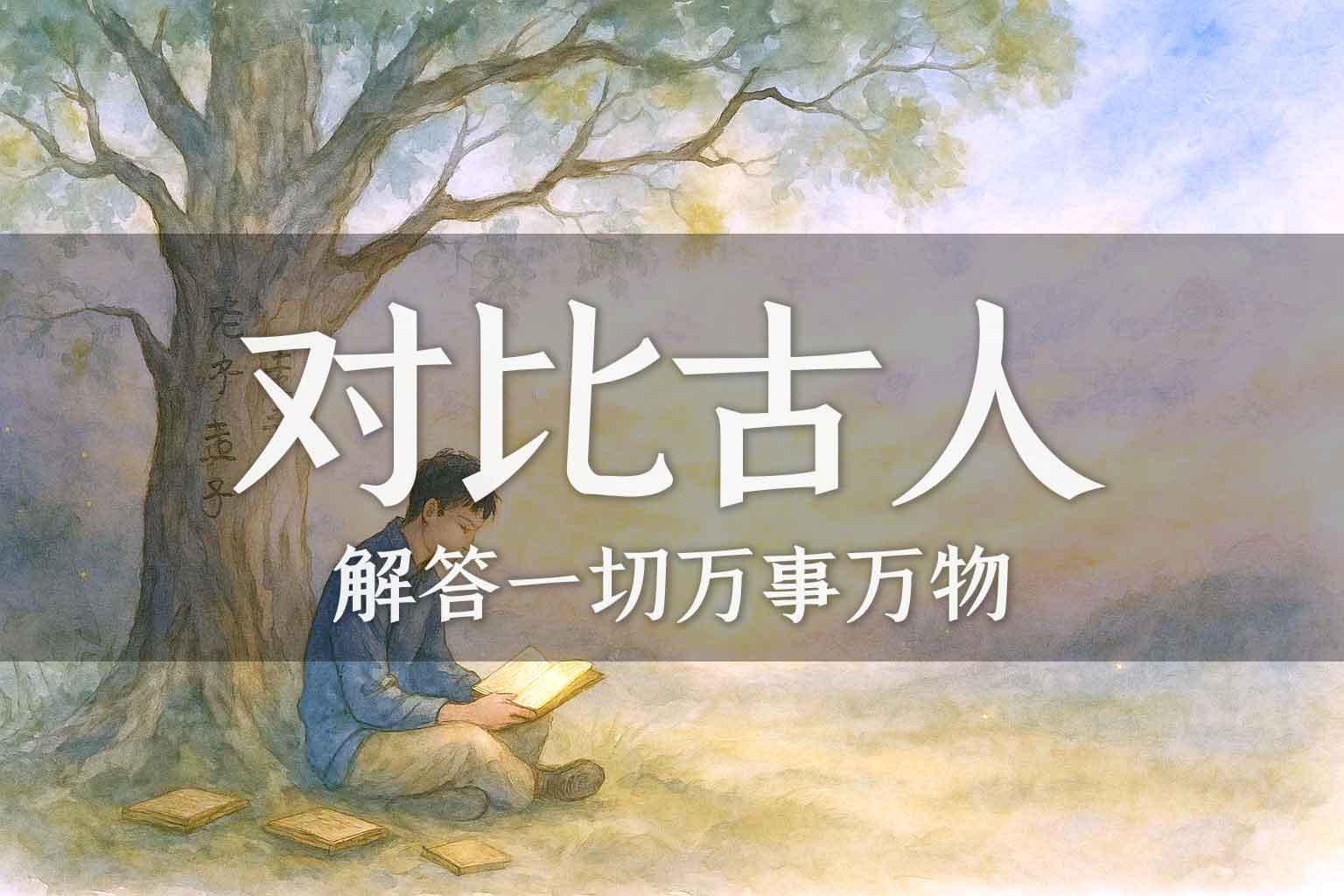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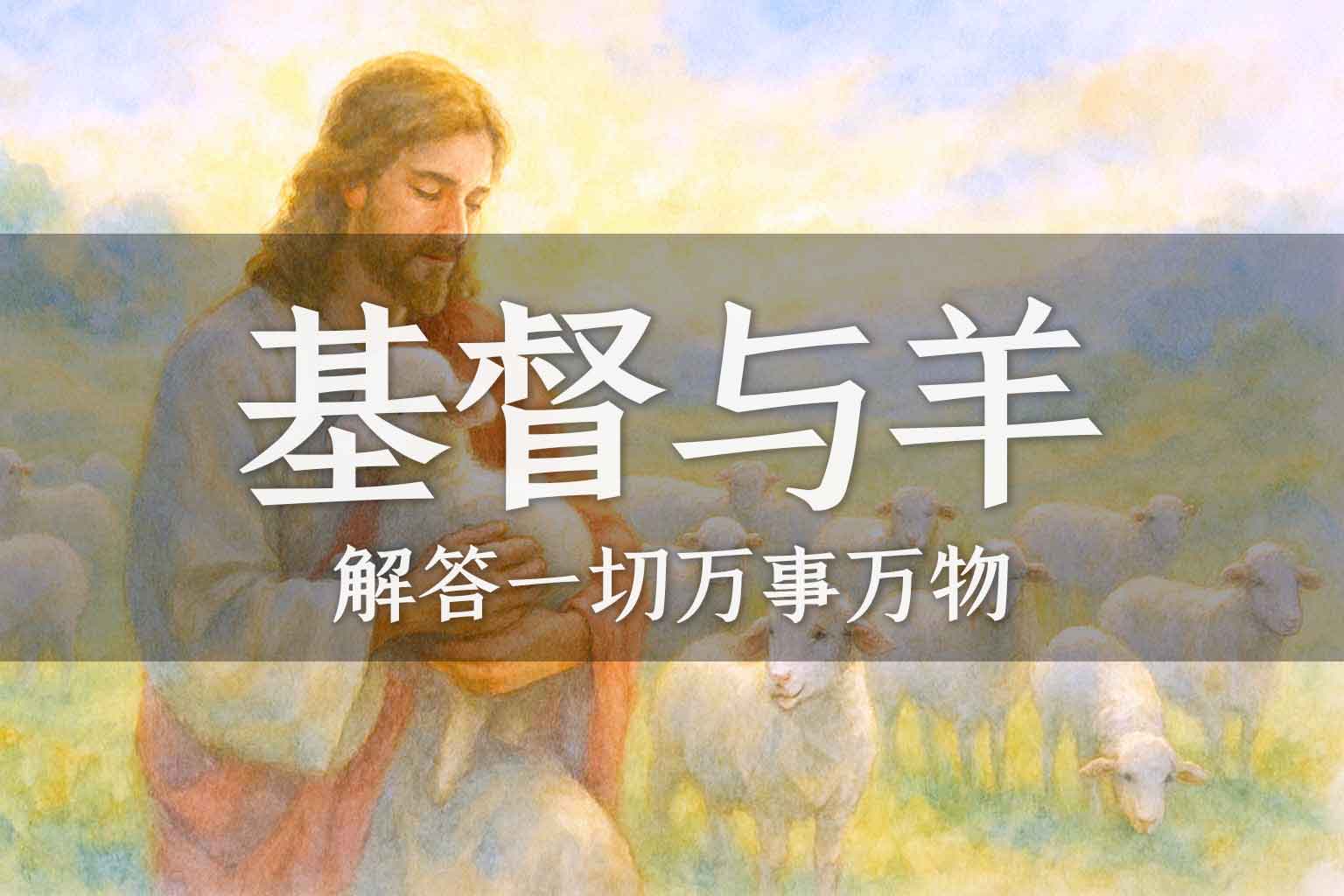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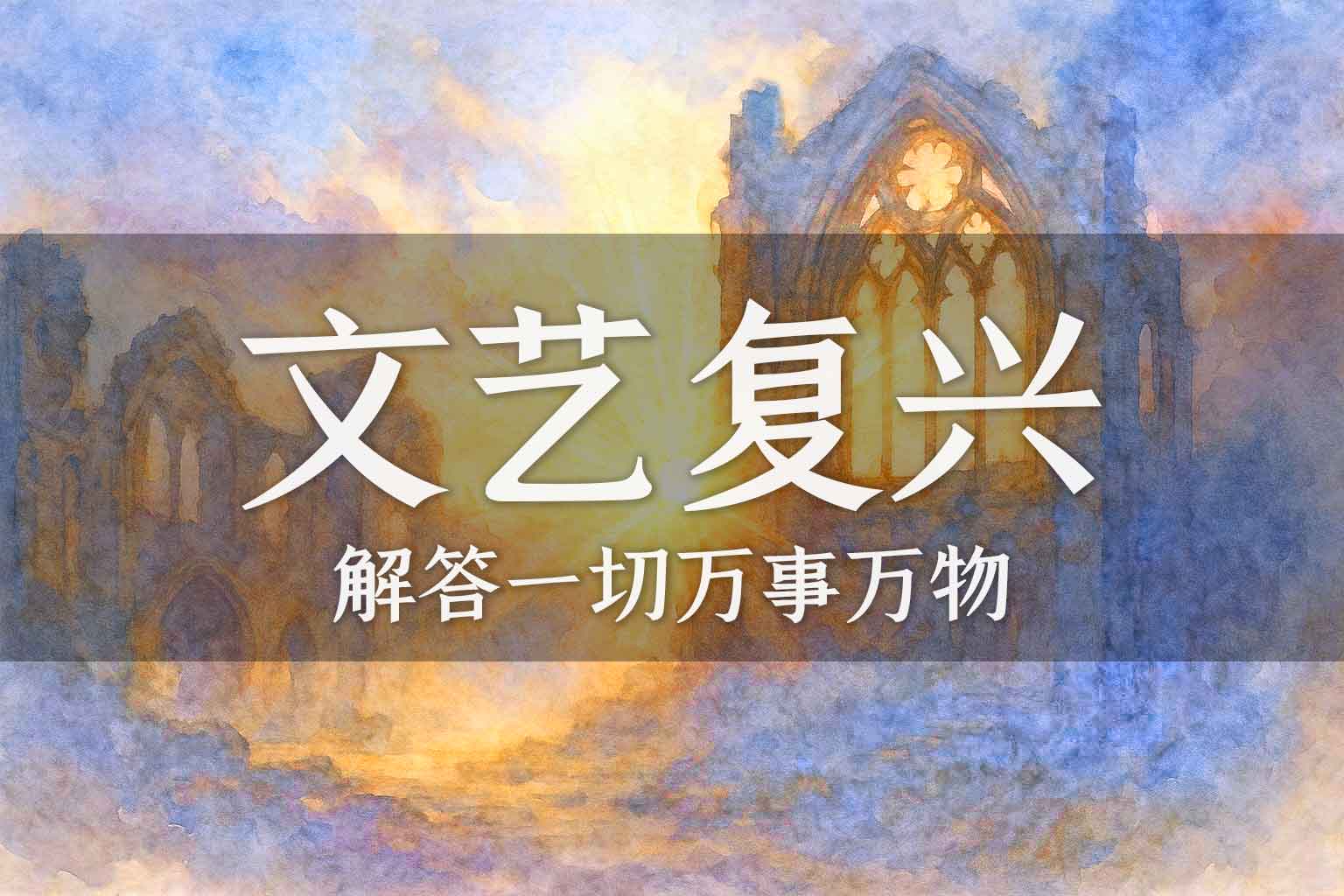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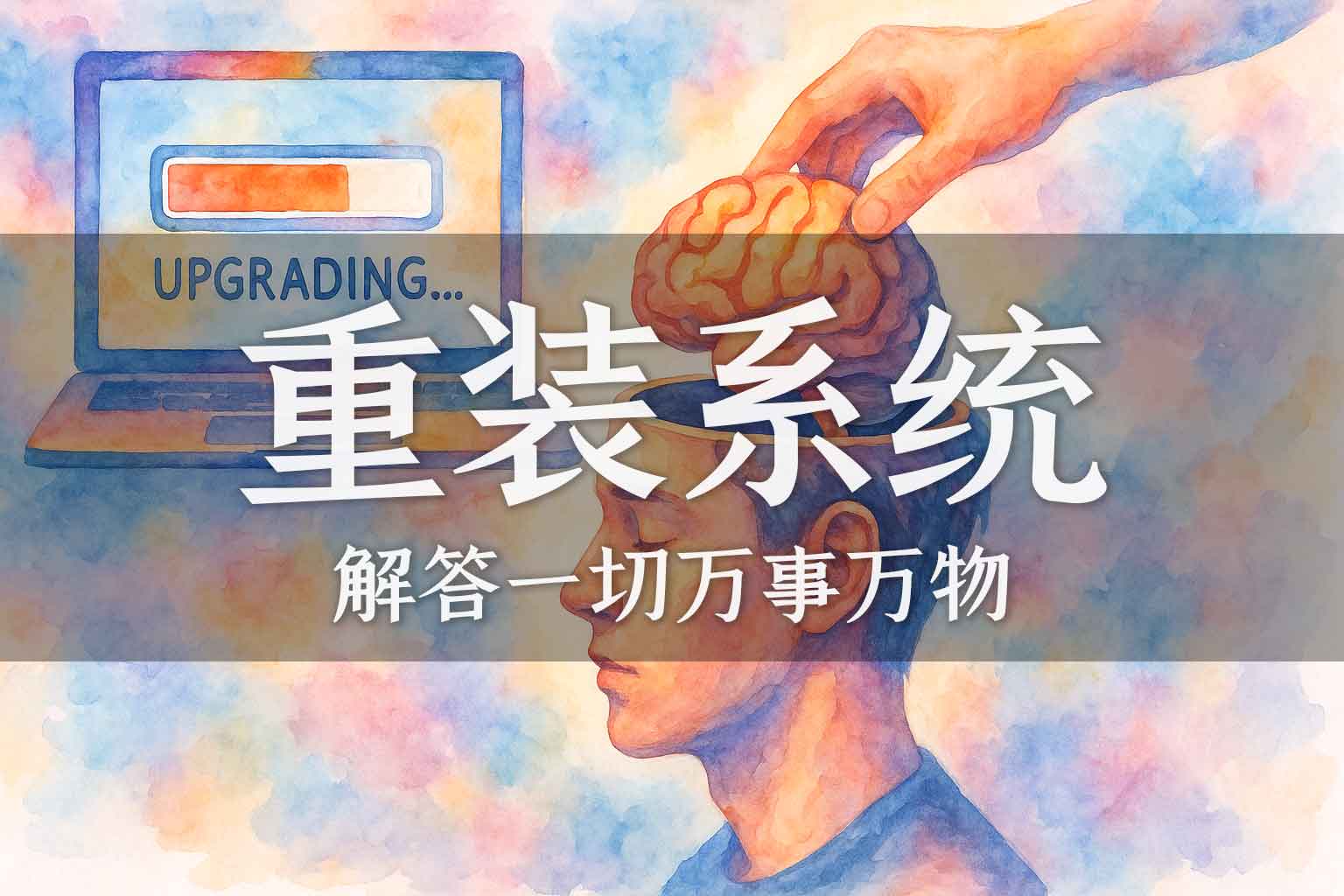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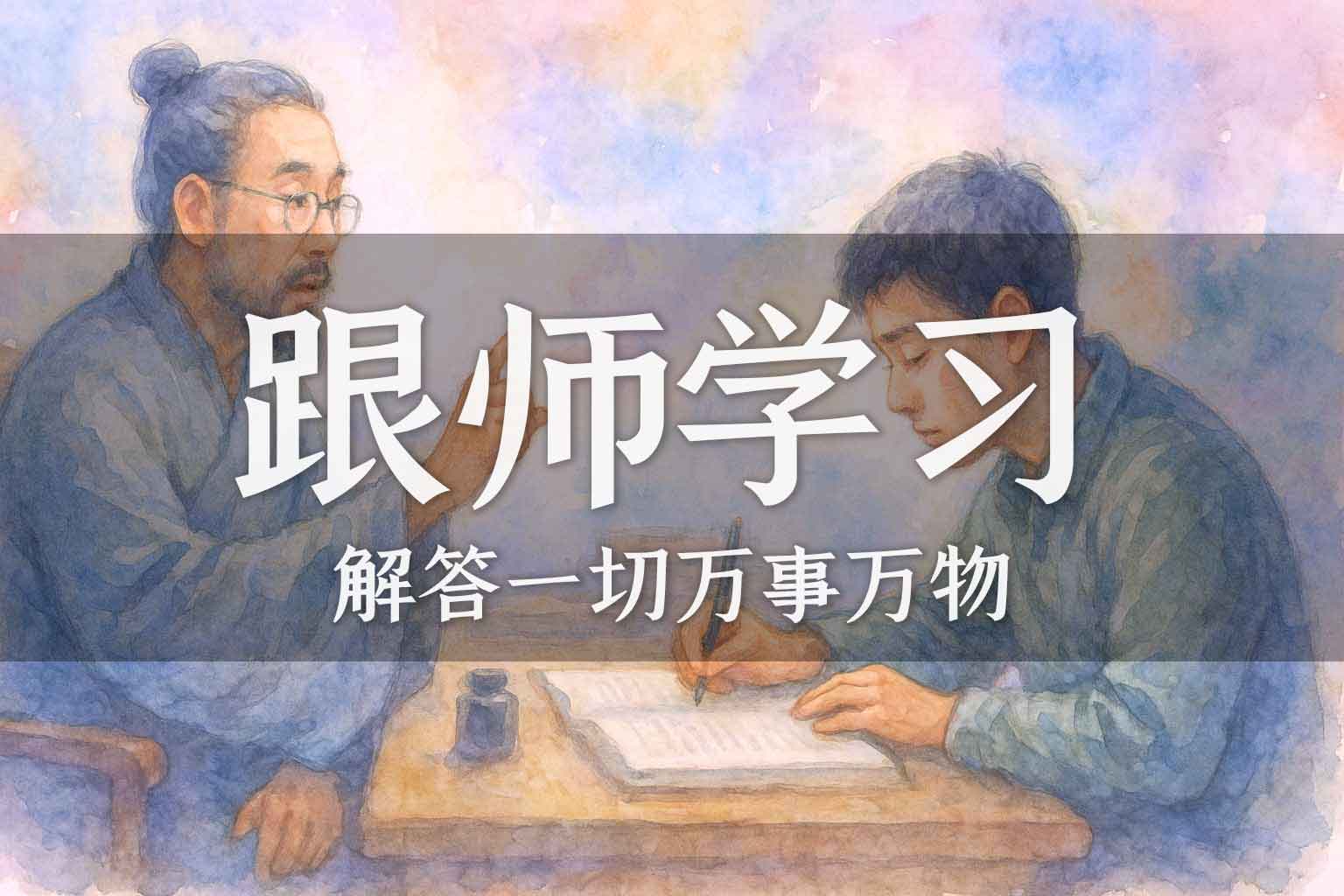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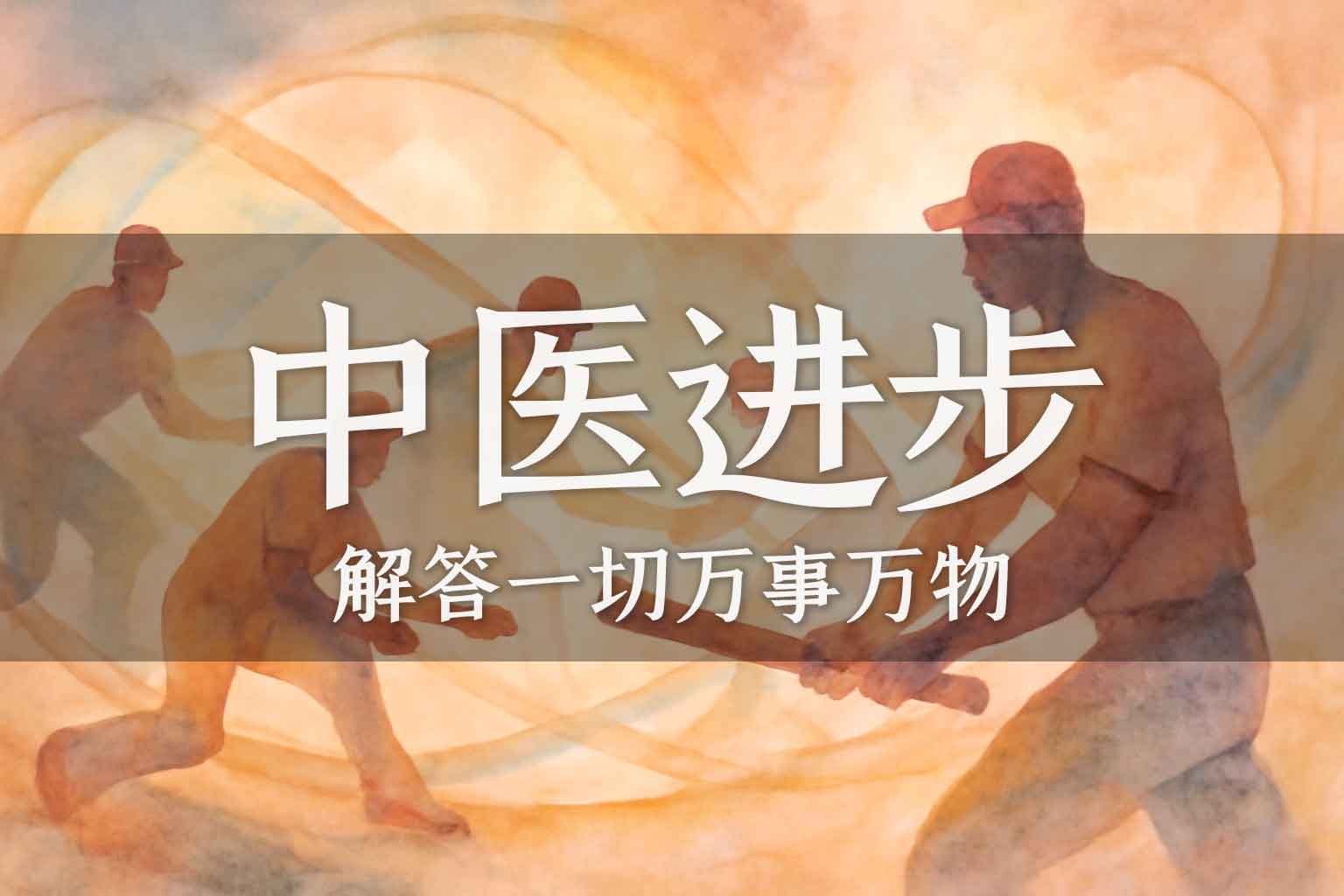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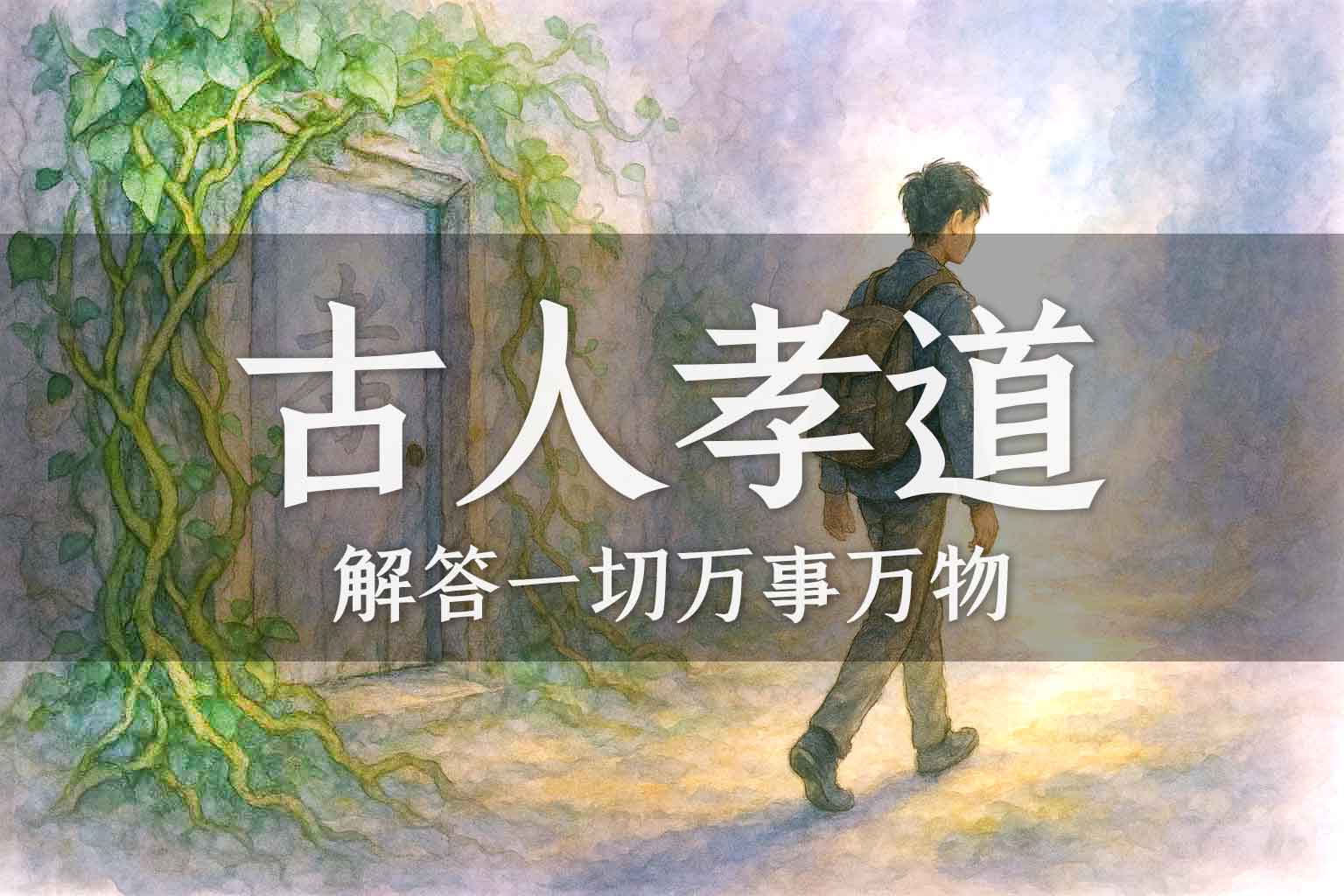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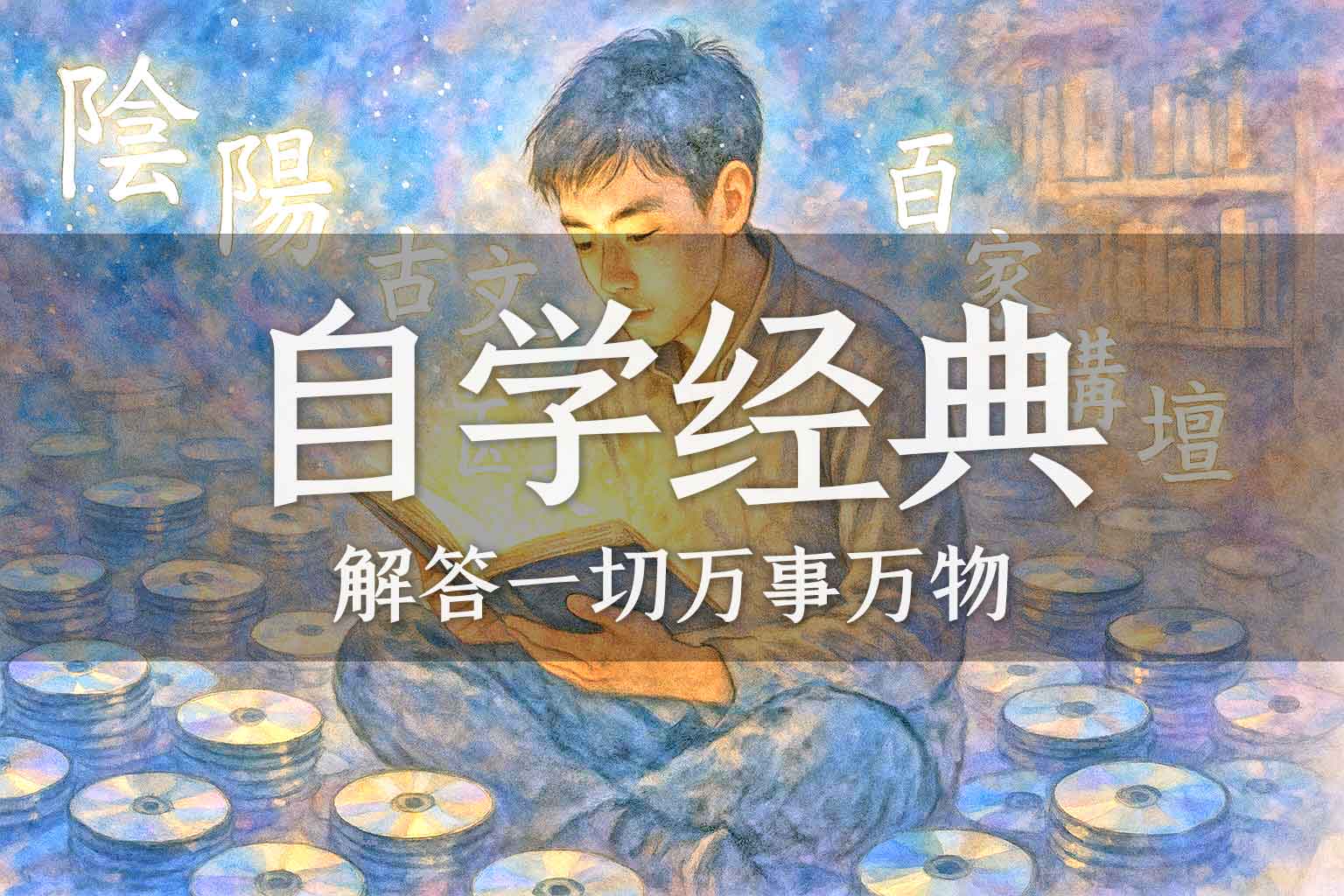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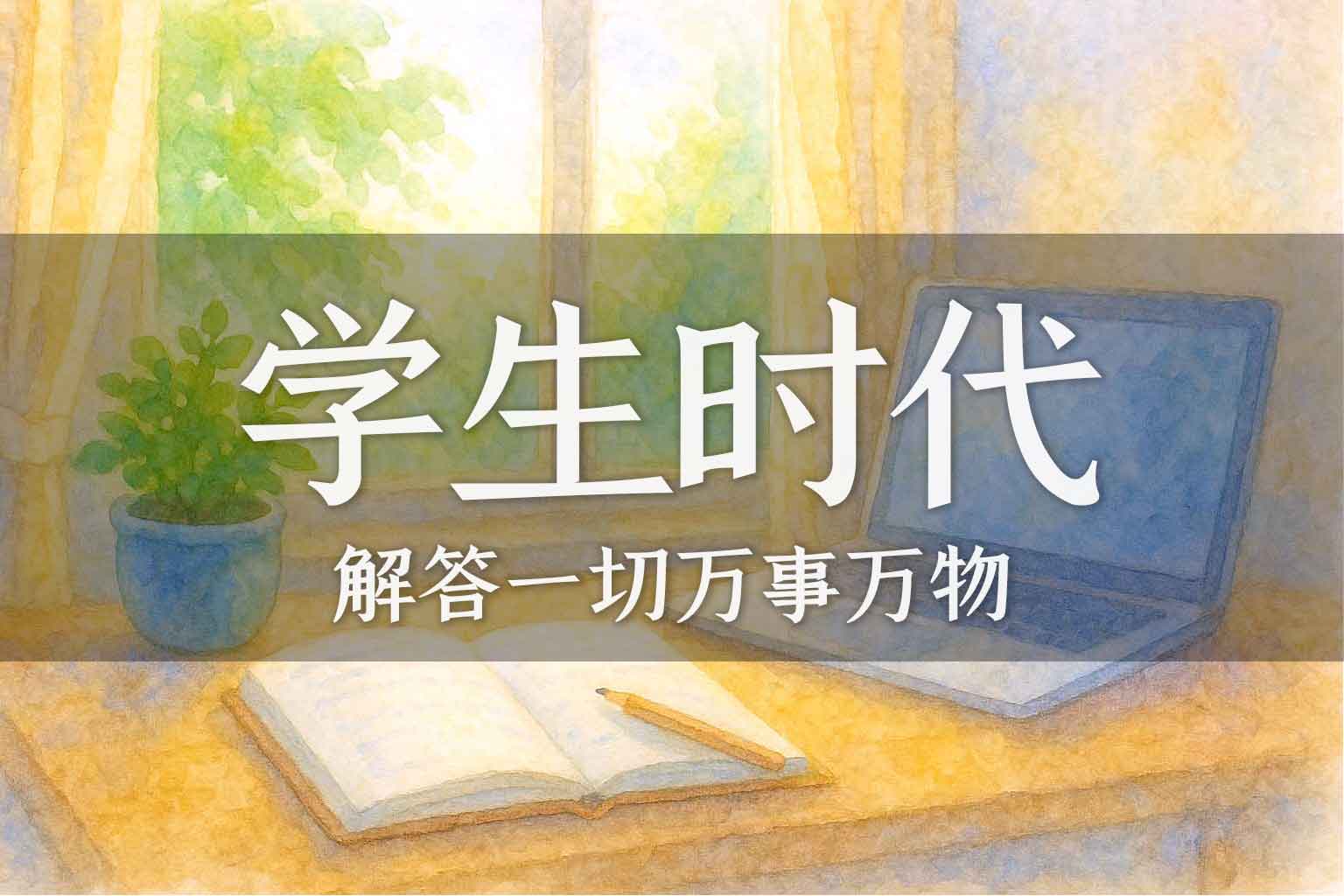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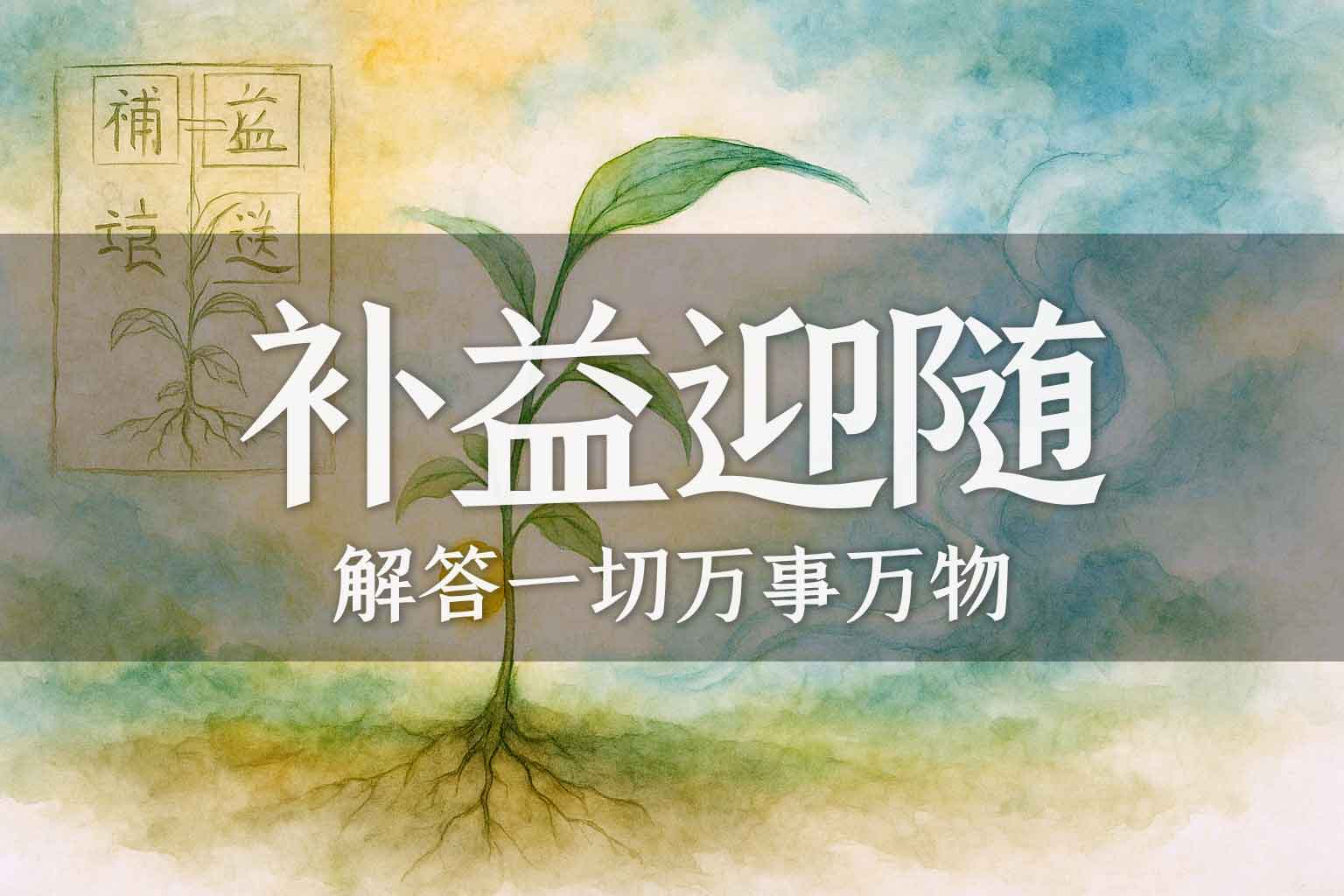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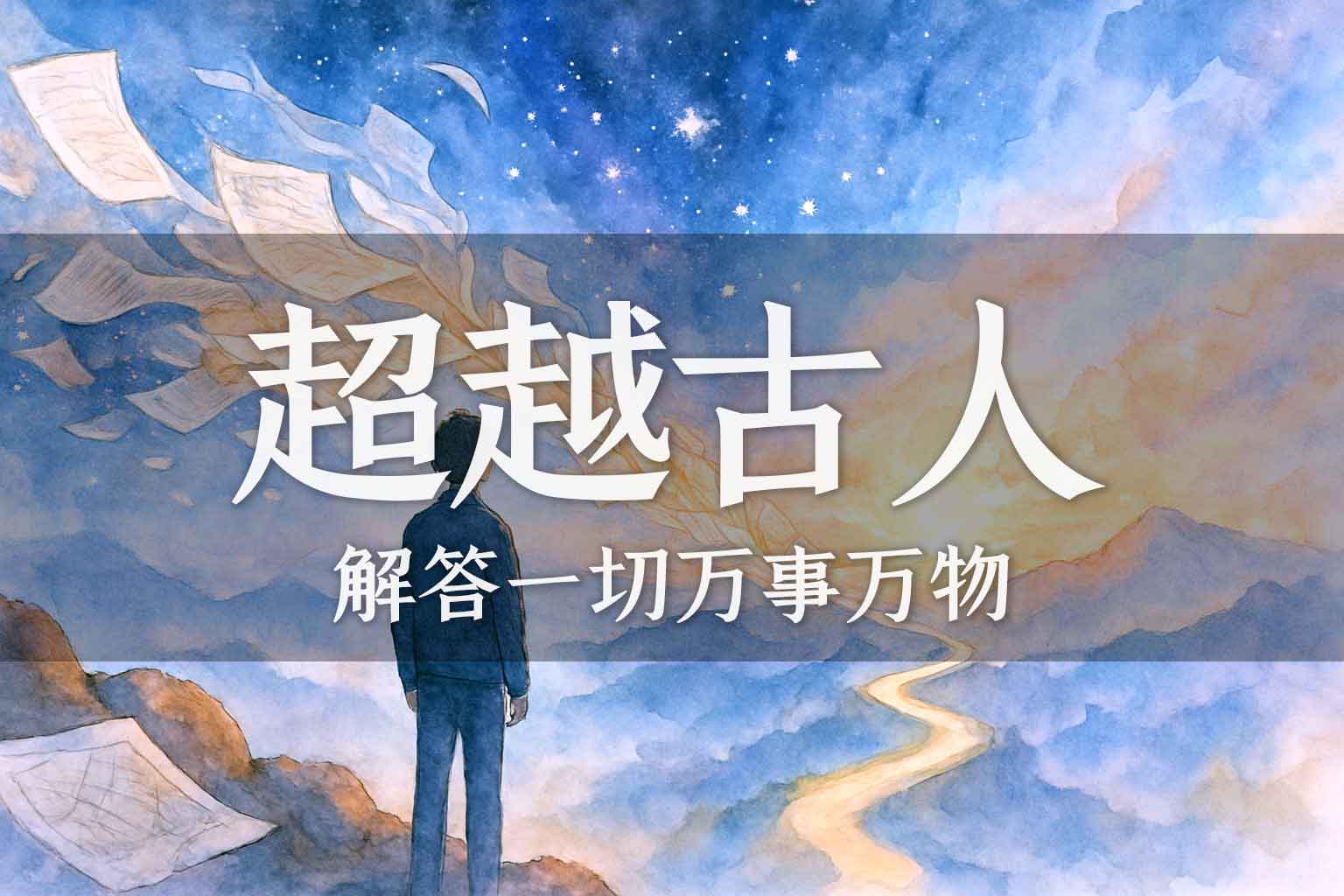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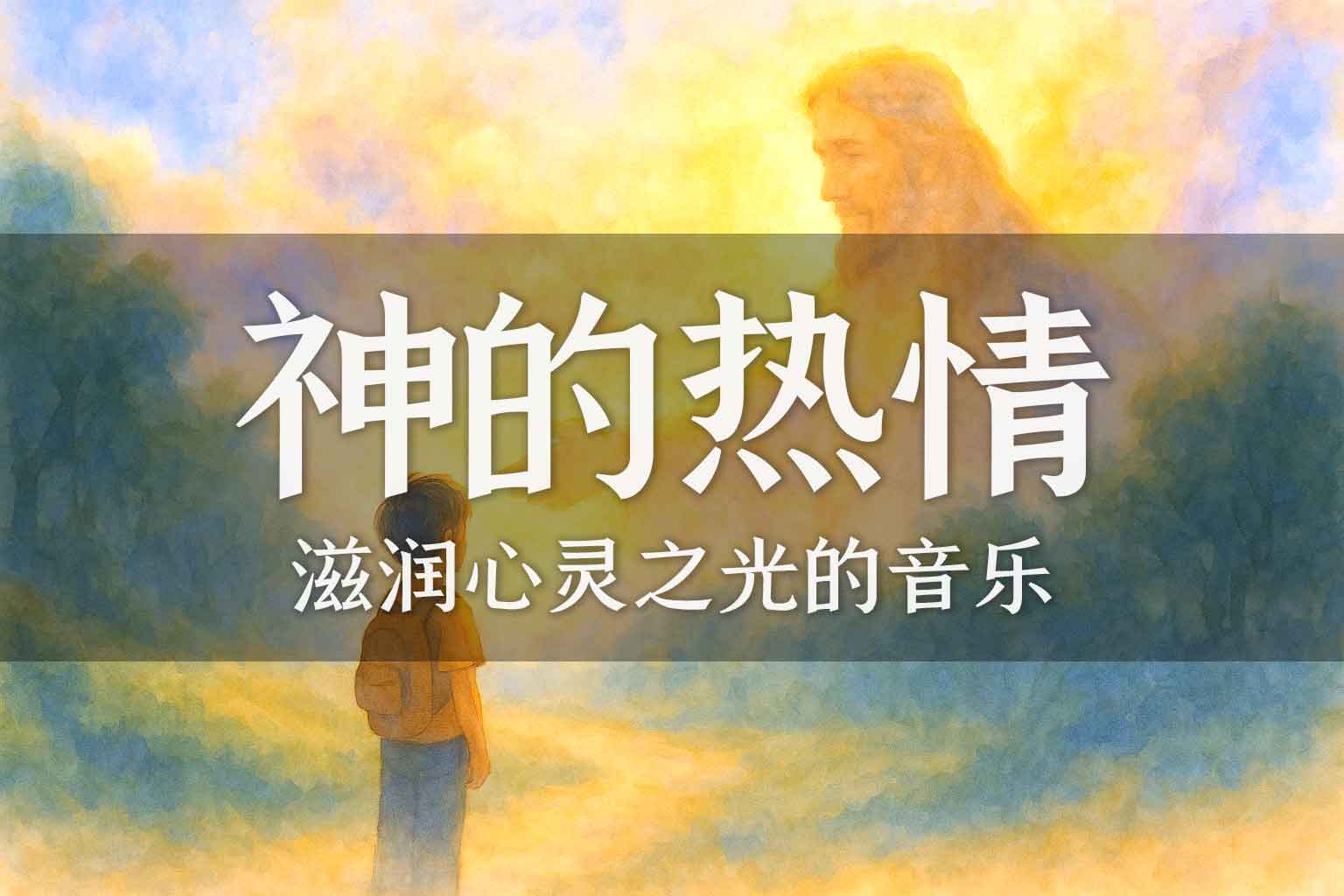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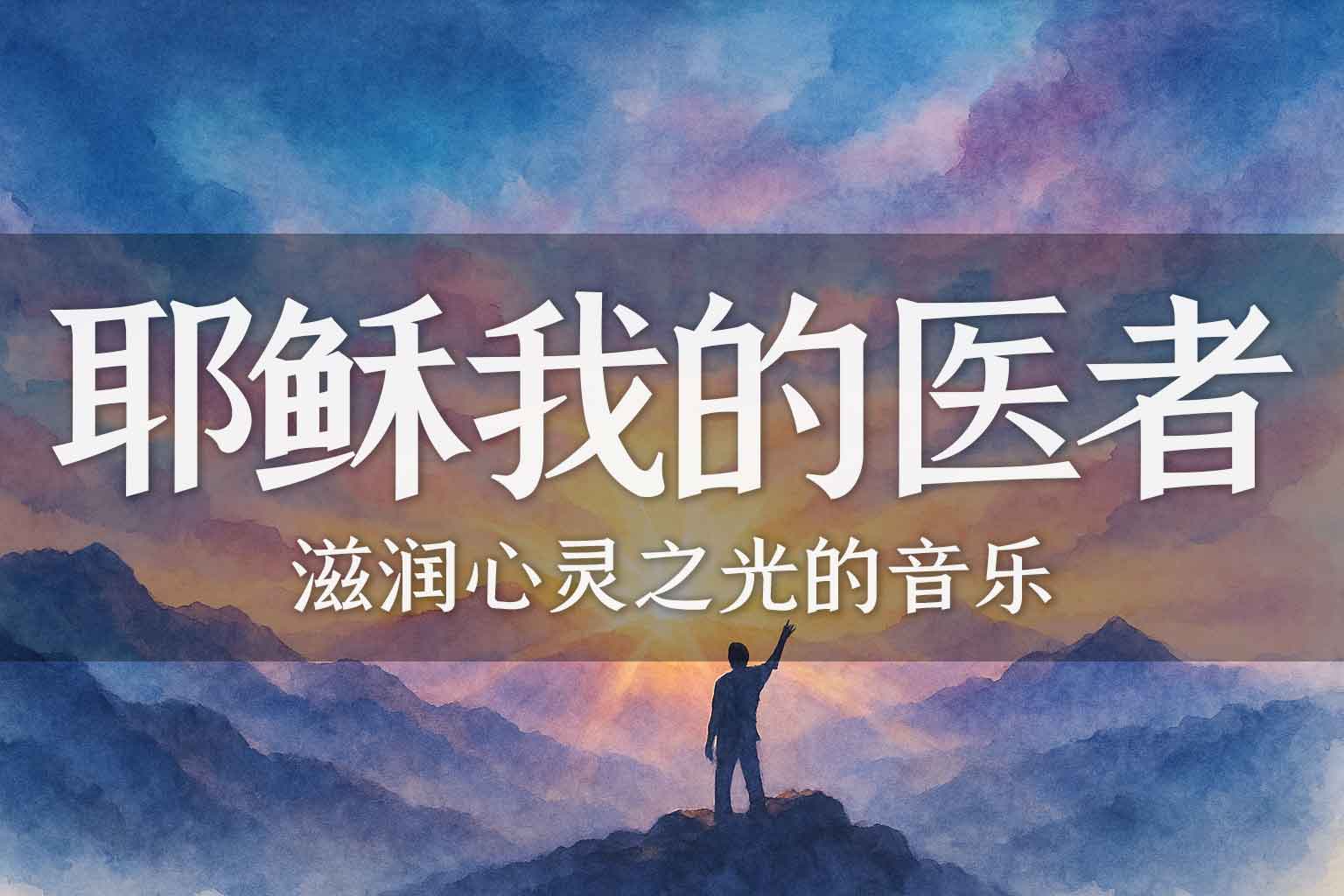

暂无评论内容